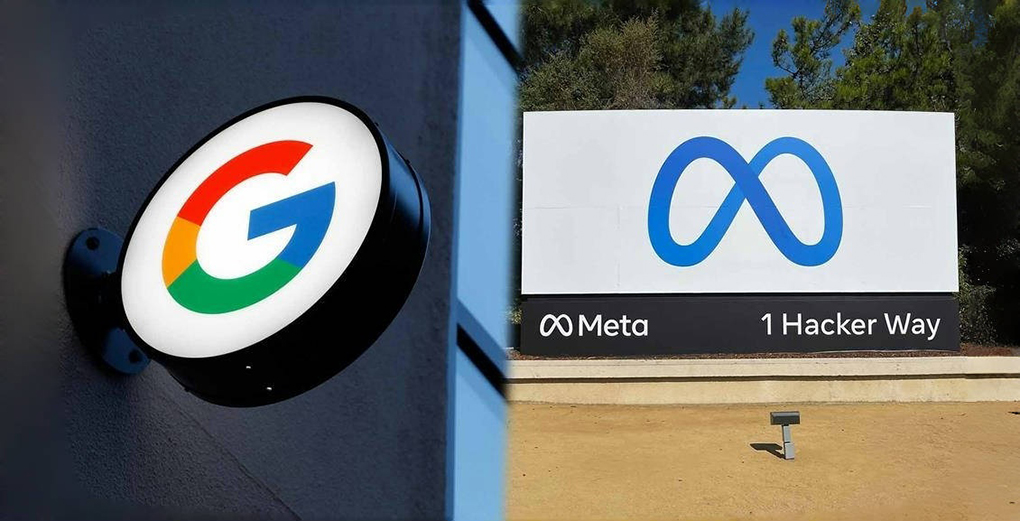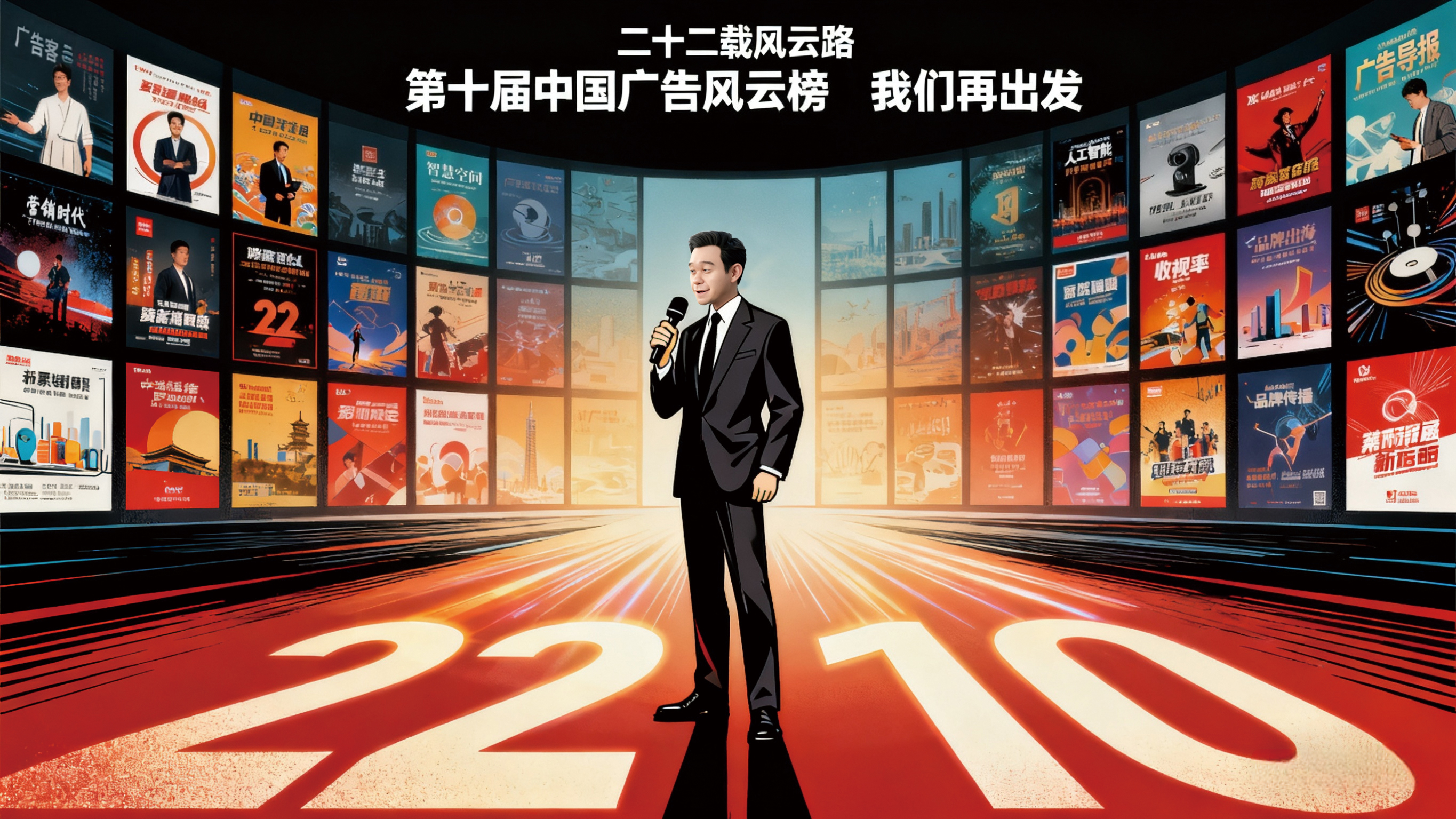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何海明教授,2016年从央视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位置离开,回归母校。
他在央视广告经营部门20年,曾担任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主任,见证了电视媒体的辉煌。作为国内首届广告学硕士、传播学博士,他以学院化的理念和方式操盘了200多亿的国家电视台的广告。
很多人认为他来学校是退休养老,或者开一门“电视媒体经营”的课程,但入校之后他的选择让人意外,他选择了年轻教师居多的网络与新媒体系,开了一门“新媒体创业课”。
现在,这门课已成为全校学生的通识课,一百多个听课名额每学期都很快被一抢而光,成为了中国传媒大学最受欢迎的通识课之一。
他是一位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授,讲新媒体创业,也带团队做账号、做直播带货,做名人探厂。
因此,学生也愿意请他做创业辅导老师,学生中有的获得了北京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有的获得学校的认可与奖励。
他说,他做新媒体很失败,但作为一名老师收获满满。最近,他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擘雅品牌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打造品牌的黄埔军校,以丰硕的成果来助力品牌建设。
01
营销生态:
“两端”“三方”的边界和功能变化
谈及目前营销生态发生的新变化,何海明建议我们从“两端”“三方”的角度,去复盘行业的变化。相对于传统的“两端”“三方”,现在“两端”“三方”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在市场中所承担的职责也处于动态变化中。这也推动了我们去联系“两端”“三方”来重新理解营销生态。
在传统的广告传播市场中,我们认为需求端是指企业主,供给端是指媒介方和代理方,媒介提供内容和平台,代理公司提供服务。
何海明认为现在的“两端”“三方”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想要厘清营销生态的变化需要先明确不同视角的站位。需求端要思考需要什么服务?什么资源?得到什么效果?供给端则要思考能提供什么媒体资源?什么内容和服务?有何不能被替代的竞争优势?
在此基础上,何海明指出营销者不能单纯从某一端的角度去看供给端所提供的或者需求端所需要的,应当将营销生态的变化视为两端多次博弈的结果。那么如何以“多次博弈”来理解动态变化的“两端”“三方”呢?
从供给端看需求端,供给端中的媒体生态在不断变化,需求端想要在媒体上显著提升广告投放效果,需要依据供给端的方法论和流量逻辑投放,并实时根据反馈调整自己的投放策略。反过来从需求端看供给端,需求端采买广告资源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作为供给端,除了售卖广告时间和广告版面外,还要思考能提供何种满足需求的产品——需求端想要“做品牌”、“做内容”、“做传播”,供给端能够从哪些方面提供“做品牌”、“做内容”、“做传播”的资源和服务。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变化,何海明举了广告效果中的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对于广告效果的界定更多停留在传播角度,但随着需求端对效果的要求走向“品效合一”甚至“品销合一”后,供给端要考虑自身能否满足这种要求,如果不满足,应该如何定位和调整,需求端则要考虑面对供给端售卖的不同资源,如何采买才能实现降本增效。这一例子正体现了两端是如何在不断博弈中互相影响,就此形成了现在的营销生态的。
当“两端”“三方”被重新定义,营销的挑战接踵而来——三方所承担的角色和职责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并且这种界限的模糊导致第三方生存空间被挤压。
站在需求端的视角,一方面,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周转率提高,市场要求企业对传播行为进行快速反馈,使企业不断收回“做品牌”“做内容”“做传播”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大量企业主历经了全方位的流程优化和数字化,提高了整合营销的能力,也很容易实现效果监测。站在供给端的视角,媒介开始布局内容和产品融合、主播带货服务等,甚至可以为企业组织现场活动、撰写稿件、发公关稿、招商活动等。
正是因为这两方都承担了营销生态中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部分职责,导致了中间第三方的生存空间被挤压。
面对这样的挑战,何海明并没有以传统的“各司其职”来建议“三方”的发展道路,而是认为这是市场的选择,“三方”都需要走出角色的桎梏,不以概念限制自身的角色,拥抱变化,迅速融合,在营销生态中以所能提供的价值来重新明确自身的定位。
以“企业开始做自身的传媒矩阵”为例,企业从过去与经销商交流获取销售信息走向直接与用户互动,试图从 “有内容”“有流量”“有用户”到 “管内容”“管流量”“管用户”。
此时的营销生态就产生了大量 “管内容”“管流量”“管用户”的市场机会,这部分需求如果传统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和文化公司不能满足,媒介方能力也有所欠缺,企业方就需要在自己的营销部门中培养相关人员来补全。
但实际上,为了兼顾降本增效和专业性,企业方还是需要大量服务于内容、用户、社群的公司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外包服务,中间方就很自然地转向内容公司、用户运营公司、策划执行公司等。
同时,在这样的变化下,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社交视频的快速发展,媒介生态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抖音每天约有两亿用户上传内容,这是传统媒体难以想象的。
一般的内容已不稀缺,用户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媒介在对用户注意力争夺的博弈中,要么选择成为平台型媒体,要么选择成为特定内容的供应商。媒体转型成为平台型媒体,首先意味着允许“媒介生态开放”,即允许上传、转赞评;其次是“商业模式改变”,即提供商业用户使用的工具,完成“去中介”“去代理”的自助下单。
媒介转型成特定内容供应商,例如垂类内容提供者、好物推荐官、顶级内容版权拥有者等,转型成功的关键则在如何将“门槛”拉开。最终,前者通过“平台化”,后者通过“特定内容门槛”实现了价值变现,也完成了媒介商业价值的重塑。
02
营销思维:
从市场、品牌与技术三维入手
以市场原理为基础力
“过去是单向传播的时代,而现在则是全民媒体的时代,过去信源单一且高门槛,现在通过移动数字媒体就可以完成与世界的连接。”何海明对比式地叙述了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的差别。互联网千人千面,数以亿计的用户每个人都有个性化需求。
一方面,媒体不转型成平台型公司,很难满足海量用户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推荐算法推就的信息茧房也强化了用户价值观的差异,官媒价值观难以引导用户。

在这种环境中,建立营销思维应当从最基本的市场原理入手。关于如何入手,何海明提到了三个问题——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和服务?它有没有竞争力?它能不能形成商业的闭环?
例如一个公司在营销生态中定义自己为“传媒内容服务商”,那么为了提高竞争力,就应当摸清AIGC的规律、效率和效果,而为了形成闭环,就应该打破限制,将所涉及的业务拓宽到脚本、文案、创意形象设计等各种形式的内容生产;同样,作为平台型媒体,就要考虑自身媒介资源的竞争力,媒介生态是否能够帮助用户完成“展示-互动-转化-分享”等商业闭环,以此为广告主提供营销闭环。
以数字营销为积累力
“2017年新媒体营销新风正盛,我在中传开设了面向全校同学的‘新媒体创业与创新’课,邀请多位在一线的行业大咖作为这门网络直播公开课的嘉宾。这门课程不仅受到中传同学们的喜爱,也借助互联网视频吸引了社会上众多这一领域内的从业者。”
何海明在介绍这一课程时,也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全民数字营销时代”的现象,各行各业的广告主,无论体量大小,都进驻到数字营销行列里,在积累中不断优化营销策略、流程、效果。
以品牌建设为突围力
行走在营销生态极大的内卷、挑战、迷失和焦虑中,品牌是高价值护城河。何海明以直播带货来展开他理解中的品牌,“在直播间里,大家会区分哪个是品牌,哪个是‘白牌’,‘白牌’是没有品牌,只是达到了物理功能。”对于名人主播来说,更倾向于卖品牌产品,因为品牌的售后、服务、质量很少让消费者转嫁到主播上。
企业最初进行直播带货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但在销售过程中,能够明确体会到品牌价值对于用户购买的影响,使得“大品牌能托场、能走量、退货率低、有利润”成为共识,大主播也需要这样的一线品牌支持。
何海明认为,随着供应链的完善,企业的制造成本越低,产品的物理性差异会变小,品牌依旧是企业的护城河。以生产包装水这类产品为例,生产线都是专门的供应商提供的,是可复制的,但品牌是顺应人的认知规律,消费者正是通过品牌形象来区别产品。
何海明还重新梳理了“定义”与“定位”之差。不同于马斯克定义汽车、乔布斯定义智能手机的“定义”,“定位”则是类似“东方树叶,0糖、0脂、0卡、0香精、0能量”、“洋河,高端绵柔白酒的开创者”等。可以说,定义是对产品的颠覆,定位则是与消费者的认知匹配。
03
未来营销:
没有“黄金法则”,应与时代同频
学科人才需要转身
企业试图以机器高效率来弥补人力带来的效果,以节省人力成本,并在多次重复实践中提升效果。
站在教育者的角度,何海明坦言,无论这种降本增效的模式是否可行,AIGC技术的出现确实对所有专业都产生了冲击,对人文社科尤甚。知识点和信息处理能力已没有多少价值,在机器的帮助下,学生甚至可以一年完成十年的课程,这也进一步要求社会重新思考教育布局的问题。
除此之外,技术也改写了内容制作行业,举个例子,过去只有央视和少数获权媒体才可以使用航拍,现在基础效果只需要prompt生成;过去内容是传媒大学的学生优势,现在内容创作也可通过机器来完成。
这些思考,与其说是思考人才的转型,更不如说何海明是在思考营销传播生态中的“人”如何站位。
过去是一年转一圈,现在是一年转三百六十五圈,个体失去了所谓稳定的“长期饭票”,已经不存在任何人都适用的“黄金法则”。
在如此多变的营销生态中,“广告人”“营销人”不翻车关键在于能够与时代同频共振。“跟得上”的营销人即使九十岁他仍身在行业中,“跟不上”的营销人即使三四十岁吃老本也很费力,未来营销人的境况很可能会发展成“跟不上就退休”,因此,何海明认为“终身学习”是永恒的话题。
媒体转型不能只“形似”
在传统媒体转型的过程中,何海明见证了大量例子,它们或转型成功,或归于寂寥,或仍在艰苦探索,流量红利见顶,现今早已不再是媒体改版、媒体融合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时代。
传统媒体转型困难在于追求“形似”,反而容易忽略“新媒体”背后的互联网基因。针对如何完成“形似”到“神似”的转变,何海明认为传统媒体需要自省。
其一,新媒体关键在于“互动”,形式是否是互动的?内容是否是互动的?与用户关系是否是互动的?大量传统媒体只是将原本在报纸、广播电视发布的信息转移到网络上,或者是将短视频形式搭载到原本的内容上;
其二,传统媒体“包袱重”,所谓新媒体正是要强调 “下载量”“日活量”“用户黏性”,关注的指标就与原有的资源型传统媒体不同,媒体逻辑迥异,更不能说一个传统媒体还没有转型成一个新媒体,就要做新媒体营销;
其三,“新媒体”强调变化和即时调整,抖音从2016年推出产品到现在,依旧不断优化算法来满足用户需求,背后是强大的技术团队和对算法的执着。
04
后记
在结束这次访谈后不久,何海明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新成立的擘雅品牌研究院的院长,和荣誉院长刘瑞旗先生去美国高校进行了访问,收获满满。
“正如北大才子李国庆在他视频号里说‘即使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尽力做到不被时代所抛弃’。”
何海明用这句话表达出他对未来营销人才的看法。
“这大概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恐惧和不甘,但终究是要被抛弃的,未来在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

2023年12月,何海明和刘瑞旗与斯坦福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教授一起合影